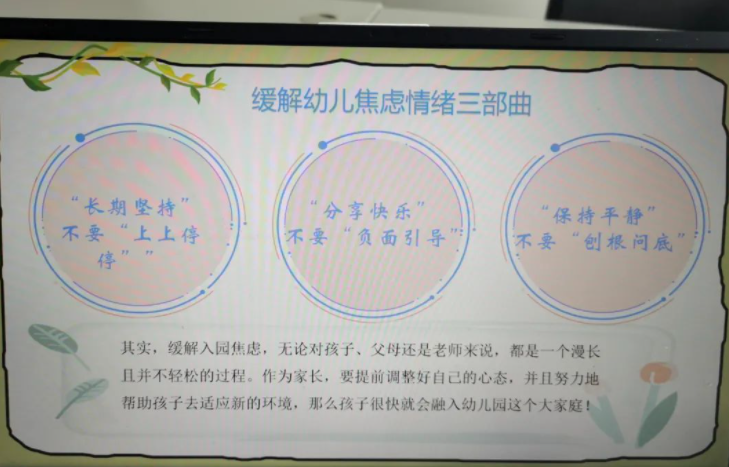人间色系
老家万荣方言中的副词甚美,有一种过于浮夸的炫耀,好像心里有万千遽促的表达,最后临了也只崩出一个字来。然而,此字却有万千的分量于其中,像就此起了重誓、缀了力道、夸了海口的一句狠话。
比如颜色,杠红、蕉绿、雪白、焦黄,闻之便在心里可劲地浓重了色深的程度,一定是能够想象到的最红、最绿、最白、最黄,连语气也抑制不住地开始铺排、渲染、夸张起来。我弟小时候还没对这些方言副词运用得心应手时,常颠倒了它们的用法,他会激动地说着自己观察后的描述,杠白、雪黄、蕉红,所有的颜色与副词都搭配错了,唯独“焦黄”不会错。因为,那是我们最常用的夸张,比如一张诱人的饼子、一块烤酥的馒头、一根炸脆了的麻花……它们的都是焦黄焦黄的颜色,都是令人割舍不去的、一种温柔而富有诱惑的颜色,与那些隐于生活罅隙中的修饰词一样,如晑(xiang)干(很干)、炰(pao)热(很热),共同构成了我们曾经贫乏而热气腾腾的生活。

当然,所有的黄并非只有焦黄一种,也可以蜡黄、金黄、杏黄,但我笃定地认为只有“焦黄”才是亲民的并且讨人爱的。蜡黄,似乎是一种病态,一副肝胆染疾的黄疽色,或是受到惊吓,伴有豆大的汗珠冒出、落下,人也变得虚垮、弱色,仿佛承受了难以抵挡的摧折。即便同样是脸色,焦黄也是主动的表达愤怒和不忿,而不是蜡黄那般垂头丧气,《于公案》中有“闻听气得面目焦黄”“气得粉面焦黄暗骂”,焦黄当然也姓焦,焦急焦渴焦愁焦躁的焦。金黄、杏黄,显然不属于平民的颜色,要么富贵,要么高蹈,要么接近于帝王之家已经独占了数千年的赭黄色。相比之下,焦黄几乎泯然于众,仿若丰饶与凋残共融的一种颜色,时常在眼前交汇漫延,一片饭滓的弥漫或者一口陶瓷的用具,都可以由焦黄扮作人间的亲密,充斥于我们稠密而又平淡的日子里。
显然,焦黄是来自身边随手拈来的比喻。虽没有屎黄那般鄙陋粗俗,不像鹅黄那样文采柔丽,也不像柠檬黄、金丝雀黄那样遥远,是一个烧饭大婶、种田老汉脱口而出的一种黄,却是贴心的比喻,似乎还暗藏了时间的迫切,耽误不得,万一过了,有百般不下的焦心于其中,似乎也在叮咛,已经黄得正好了,再黄就焦了,已经黄得熟透了,再黄就过了,那么,是饼就趁热吃,是麦就趁熟割吧。你也不必拿什么蟹黄、桔黄、橙黄哂他见识小,他可能这一辈子都无缘那些高级的、不着边际的黄,但他的焦黄一定是正经正好、可丁可卯的黄,不在其中,不谙其妙。如我们幼时埋在灶灰里慢慢焦黄的馒头,烤在田间枯叶中煨至熟软而渐趋焦黄的薯类和玉米。嗯,当然还有冬日炉箅四周放置的吃食,温暖而呈现焦黄诱人的颜色,有扑鼻的香气在四周弥漫开来。
焦黄,成熟之色,是大地上呈现谷物成熟的独有之色,也几乎是所有烤制食物最终定型的成熟之色。北方,焦黄的大地上焦黄麦子,南方,润绿的一色江南有稻子焦黄地熟了,花木成熟也多有焦黄之色,清人陈淏之园艺著《花镜》中有花“胜金黄”,颜色亦焦黄多叶谓之“胜金”。上溯至远,人类学会用火之后,最早品尝到的先是肉食的美味,但后来,谷物加热烤炙之后的熟美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焦黄由此而生,为焦黄乐意伴奏的成熟之味是焦香,食镬之味。可以确信人类领略烤制食物之美后,这一烹饪方式燃起的熊熊火焰从此再也没有熄灭,不仅焦黄了东方的饼馍包子,也焦黄了西方的面包披萨。新疆朋友寄来的馕饼来自当地维吾尔族师傅阿不拉·托乎买提亲自烤制,馕表面光滑、颜色又是人见人爱焦黄色,不仅味美口感亦美,让人想起唇齿记忆中家乡的新绛饼子、稷山麻花、万荣火烧。
作为原色,油画黄色是调色板的重要组成部分,据说黄色也是梵高的最爱。想必黄色系列颜色中那些“黄”成一片的淡黄、土黄、桔铬黄、深铬黄、中铬黄、铬柠黄、镉柠黄、印度黄、麻斯黄……总有一款能够呈现出始于谷物成熟和烘焙成品的焦黄色。我不懂美术,有一次观摩博物馆收藏的文明初期陶制品入神,吸引我的不是它们繁复的花纹和形制,而是陶器中存在的红、棕、黄诸色,这些以红陶居多的颜色中我竟然联想到了焦黄。一种陶土烧制成器的黄色,发红,类橙,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主流色调,由土黄原色而来,再准确点说是由黄土烧制焦黄的变色。在我盯看入迷之际,漫天漫地的焦黄扑面而来,仿佛幼时那些抖落一身灰烬的熟物,携熟悉的焦香盈盈而至。

 污话社
污话社
 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
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 难得孤独
难得孤独 雪后登乌云界
雪后登乌云界 用笔记本记录美好生活
用笔记本记录美好生活 春天的一封信
春天的一封信 打造“超长待机“能力
打造“超长待机“能力 绝不天真,绝不退场
绝不天真,绝不退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