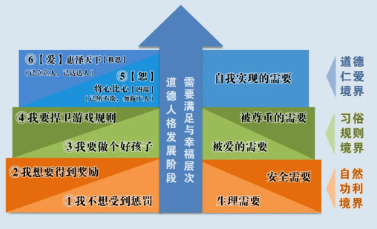上个星期,省城几个同窗旧友结伴到江南来赏秋,我陪他们去九华山间走走逛逛。
秋色真的在不经意间悄然将连绵起伏的山峦浓妆起来,无论是远观,还是近看,总有些许多让人沉醉的美好。同行的俗世奇人程瞎子常挂在嘴边一句话:年少不知少妇好,错把姑娘当个宝。可能少不更事的姑娘还未被岁月烟火浸染过,虽纯净天真,却少有生活的滋味,给人以甜,却难以让一个饱经沧桑者沉醉。
江南的秋天,愈往深处走,愈能让走过路过的人沉醉,与年龄无关,与心情也无关。入秋以来,一场又一场的秋雨滋润着江南的山山岭岭,直把满山遍野的植物变成大块的绿色,大块的红色,大块的橙色。书上读到的层林尽染一词,在江南的秋风秋雨里演变成了一种动态的美。你上午去看过一座山,下午再去时已变了色彩;你今天赏过的一片层林,隔天再路过时,又会忍不住停车坐爱枫林晚。

赏过江南秋色,几个旧友临回城时,硬拉着我上车,到城里醉一回酒。那两天我在省城闲逛时,江南茶溪小镇友人李兄告诉我:葫芦塘一户人家重新打理院子,诸如腊梅、桂花与山楂、梨子树都不要了。户主称,若是没有人家要,就叫师傅来统统砍掉扔了。砍掉太可惜了,看看你家院子可需要补点秋色,移栽一些过来。他随后给我发来一些实物图片。
丹桂飘香,腊梅怀春,山楂挂果,梨树余香,砍掉扔了确实可惜。李兄见证过我初到江南时,曾费尽周折从江北矾山移来两车蓝莓树,栽过不少果木树与花草。还在一年初春里趁江南一处园林“腾笼换鸟”,便宜买下所有的映山红,灿烂了茶溪一个春季,我为这些花草树木写过不少诗文。李兄诗文与书法都至高境,他用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:补秋。
是的,那年春天的映山红花开时节,我曾写过一首短诗,被作家出版社编辑选来用在《茶溪听雨》一书的封底:
“一夜的喜雨
润透了你的身心
所有的期待
都在早晨这一刻绽放
你艳惊了时光
将欢喜灌满我的心海
我要告诉每一个来访者
我是个幸福的人”
那些映山红在那年夏天都枯萎了,当地老农说,以前烧锅还行,潮的都能烧得着。现在不烧柴禾灶,没人要这东西。在我心里能够“艳惊了时光”的这些花木,在老农眼里当烧锅料都还不行。倒是这首诗,成了那季映山红的绝响。
花草树木在何园生生死死,我伤感多了,便悟出一些别样的道理来。花草树木原本没有贵贱之分,各有其美,能以最美的样子活在人间,添几许美好,就有其价值。至于,这花那树所谓的“贵”,也多是别有用心、赖以谋财者吹嘘而已。大愿文化园入园两旁的银杏树,当年负责栽培的园艺人告诉我,一棵树花五万块钱从山东移栽来的。我初建何园时移栽四棵银杏树,一棵千把块。再假以几年时光,长得不会比那些树细。
花草树木,懂的人自然懂了,信的人由他去信吧。你赏与不赏,它们都那么活在人间。朝山拜佛时人人口念“阿弥陀佛”,下了山回了城,一切照旧。我就见过太多的城里人,起早急匆匆上山求菩萨,三柱香后,下山觅食,又急匆匆返回城里,应对晚上约好的酒局。大慈大悲的菩萨,也只能忍看人间悲喜剧天天上演。天雨虽宽不润无根之草,佛法虽广不渡无缘之人。
我在城里一场接着一场醉时,友人李兄在声声催我回江南“补秋”。我让妻子去那户人家看看,取喜欢的先让人家别砍掉了,待我回山里来挖。
人在不同的年龄对花草树木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年轻时候忙于生计,追求理想,警惕玩物丧志,生怕沾花惹草会消磨掉斗志,没有多少心思用在花草树木上。即使偶尔养几盆花草在家,也可能转季便枯萎了,剩下一堆空花盆。有人在阳台上盆栽几株辣椒、西红柿、小葱,既装点了日子,也可救急当菜。
上了年纪的人,反而对花草树木多了几份用心。我曾去过徐悲鸿女儿徐静雯教授家中几次,她家是一所大学里一栋二层独栋小楼。她先生曾担任这所大学副校长,坐在书房书桌前读书,每次见到我时,都起身冲我笑笑。冬日阳光从窗户斜照在他的脸上,笑容很慈祥、好温暖。他们家每个房间都放一两盆盆景。徐静雯说这些盆景都养了许多年,成了他们晚年最好的陪伴。院中有丛竹子,有棵枇杷树。她说爸爸生前喜欢画竹与枇杷,栽此也是种怀念吧。
我从城里回到江南山中,妻子几次催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去挖树?我都默不作声,读书写作间隙,清理自家院子杂草枯枝,择合适位置挖了几个坑,灌水湿土。每次都累出一身大汗,也不提去葫芦塘对岸人家挖树的事情。
我在等一场秋雨,就像很多人年轻时候等远方恋人的书信一样。
昨天早晨,我在院里读刘亮程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,里面收集了他上世纪九十年代间作的七十篇散文。据称是“中文写作的垂范之作”,用一本书创造了一个家乡。看人家吃豆腐牙齿快,反复揣摸后,觉得自己这几年在山中所作收录进《葫芦塘》的七十余篇散文,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。七月下旬动笔修改长篇小说前,我花费两个月对这些文章梳理、润色,再回读时依然很是心动,可还是克制不急着出版,先放一放。今年,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两部散文集,共计四十多万字了。全靠同学和友人的资助,特别是鹿雨的无私帮助与支持,让我铭记在心。若再多出版书,与世不知有无益处,于己倒真成了负担。
江南文友汪皖平今早来信说:路遥划完《平凡的世界》最后一个句号,将圆珠笔扔向窗外,说:“去他妈的,文学。”他获茅盾文学奖时,打电话让在外出差的弟弟速回来,帮他凑路费进京领奖。弟弟愁肠百结说,你可不能获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了,我凑不出来美元让你出国领奖的。路遥四十二岁死了,用不着麻烦弟弟了。农民耕田吃粮过日子,我闲在山中不舍昼夜写作,再苦再累也不会骂文学“去你妈的”。我知道文学不能当饭吃,趁能写时就写吧,文章与书稿放柜子里总不会问我要饭吃。
吃早饭时,我查看青阳天气:秋雨要来九华山中,连下好几天呢。我告诉妻子:去挖树。她忙找齐铁镐、铁锹与撬杠,推着板车去葫芦塘对岸人家。
我算是喜欢体育锻炼的,要问我什么运动最能锻炼身体,我会首推:挖树。挖树极需要体力与耐力,挖得你一身大汗时,树身依然纹丝不动;挖得精疲力尽时,还不知道竟究是哪一条主根不肯舍离故土。
我们跟邻居打过招呼后,先挖的是一棵腊梅树,树高二楼,比我想象中的要大,开挖远比我以前挖的树要难。树身一侧紧挨着游泳池,铁镐用尖头一点点掏土,往深处掏,到后来只能用手抠土。带去的一水瓶水喝光了,汗透衣裤。妻子在一旁说要不回家歇歇,明天再来挖?凭以前的经验,挖到最难以坚持的时候,两强相遇勇者胜,再坚持五分钟就可能别开生面。
无数个五分钟坚持下来,腊梅树终于动了芯。妻子喊来环卫、家政一群男女,竹杠、麻绳、尼龙布全用上了,众人发一声喊,将腊梅树拖离了故土,搬上板车。这情景让我想起从前农村嫁姑娘出门时的场景,养大的姑娘离别娘家时都是万般不舍的,原本一家人往后就成了亲戚。我握车把手往前走,众人在后面托着树枝推,却越走越重,前所未有。有细心人喊:“两只车胎全瘪了”。新娘上了轿,只有往前抬着走了。我们硬是这样将这株大腊梅树移到了何园,妥妥当当的移栽进挖好的坑窝里。
当天下午,秋雨如约而至。爽爽的秋雨里,有点点凉意。我在书房沏上一壶茶,文学先放下,凭临窗户,欣赏这窗户下面新栽的腊梅花,总觉得“补秋”补得恰到妙处。以往的冬夜里,我独自在山间清冷的屋里写作,小狗阳阳乖巧地卧在脚边,给我许多温暖与感动。往后的严冬寒夜,写作累了困了,开窗嗅嗅窗外这株腊梅花的香味,会让我在文学的寂寞旅作中“再坚持五分钟”。
秋意凉,冬季随后就要到了。再难再苦,我也要坚持给这缝缝补补的人世间增一缕香,添一份暖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污话社 » 我在秋雨里挖呀挖呀挖……

 污话社
污话社
 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
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 难得孤独
难得孤独 雪后登乌云界
雪后登乌云界 用笔记本记录美好生活
用笔记本记录美好生活 春天的一封信
春天的一封信 打造“超长待机“能力
打造“超长待机“能力 绝不天真,绝不退场
绝不天真,绝不退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