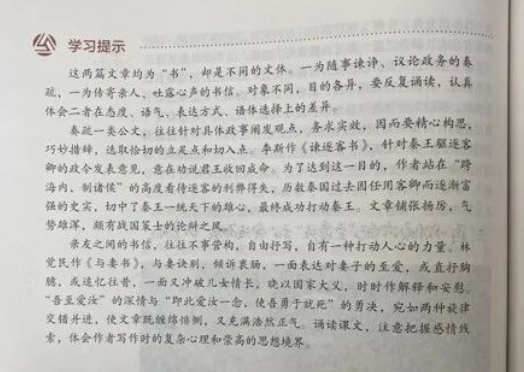贤山寺是关中的一座名寺,它载满了历史的厚重,但对我来说,它就像我家的院子,我是它的一个孩子。对它的认知,多来于感性。
——题记
贤山寺是一座和我有感情的寺院,因为我从小生活玩耍的主要地方就是贤山寺,在我的概念里,贤山寺不单指一座寺院,它还包含了这座寺院所处地的这些沟壑和林木,野花和野果,蜂蝶和鸟雀。
我在小学至初中的时段里,不是在学校,就是在贤山寺,和贤山寺结下了很深的缘分。以后虽然远去他乡,但只要回老家,总是要去贤山寺看看,如同内心深处所指的真正的回家。

今年年内,我去过三次贤山寺。一次是我一个人去的,虽然年迈的老母亲一再的让我别去,现在太偏太静太少人气,但我却深入沟底,找到了很多少年时摸爬滚打过的痕迹;第二次是和三个孩子一起去的,小女儿太小,沟沟坎坎走不了,所以站在沟边平坦的地方看了看,主要看了村里老太婆们供俸送子娘娘,药王等神仙的贤山寺,还专门绕河去看了香山居士的坟茔;第三次是单和儿子去的,儿子顽皮好动,很喜欢攀高下低,所以我带他去了烂城。名附其实的烂城,烂的没有了一丝儿城的痕迹。儿子总希望能从那些黄色泥土中找到古代人的兵戈或者箭矢,结果是跑了很多地方,除了摘了些酸枣外,也没找到什么。烂城在贤山寺的东南方向,一片百余亩地的高起平台,四周悬空,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入,四周的围墙还依稀可见,但中间的建筑早毁,我去的时节,玉米长的很丰茂。
贤山寺只所以为文人墨客惦记,主要是它地理偏僻幽静,风景秀丽,地形特异,我想这是最初的因素。
和贤山寺素有渊源的人有:
贤齐,这似乎是贤山寺有记载的第一个人,传说他凿洞居住在贤山寺,有两虎守洞,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意思,是神是人,有点掰扯不清,而且还有元顺帝拜贤齐为国师的说法,我没有亲见过第一手的记载,道听途说,不足为记,而贤山寺大约从此来。
张载,有说在贤山寺读书,有说在贤山寺讲学,总之跟文化有关。午井镇的名字也跟他有关,还有贤山晚照为扶风八景之一,也跟他有关。说真的,贤山晚照是确有其事的,就是天至黄昏,远处都已进入了昏昏的夜幕之中,唯有贤山寺的沟涧如有灯照,而且须得是个巨大的灯,树花俨然,明亮如昼。这个景应该真正看过的人不多,大多是听闻而异,我从小在贤山寺玩,晚上天黑仍未回家是常有的事,所以亲历的次数是数不清了的。
杨博,这个人我不是太熟,基本上就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杨博,和我的一个侄儿同名同姓。但贤山寺的院中有一通杨博的贤山寺游记碑刻,文采斐然,保存的也是相当的完整,没有任何缺损。这也是目前寺内我所能知道的一件有文化、历史价值的东西。如果我儿子知道了,一定会问我,这个能值多钱。
关于这一块碑,我所知道的有两点:其一,文革中拆除古贤山寺的时候,确实是有人偷藏了这块碑,埋在土里多少年,直到重建时,才告诉了寺僧,让该碑重见天光。其二,据说有人考证过这块碑,是在唐原碑上重刻的。而且只是磨掉原碑文字,上端的佛像造型仍然保留,并据此说贤山寺的历史可远溯唐代,要我说,也许吧!虽然我也希望贤山寺的历史久远到无限,但以此为据,明显单薄乏力。
憨休禅师,今年某天突然接到扶小风发来的另一篇《游贤山寺记》,是憨休禅师所做,文风高古,意远境幽,才知道有憨休禅师这么一个人,也对小风刮目相看。这是一篇纯古文,无句读,小风断了句,加了标点,我觉得个别地方不合适,进行了修改,和小风综合了一下,觉得基本应无错讹。后权敏也断过句,觉得他断的问题比较多,当然这跟他对贤山寺了解少有关,他的古文功底还是很硬实的。
王元中,绛帐人,贤山书院是他经历了很多困难组建起来的。在当时国民教育缺失的情况下,培养了很多人才,这一方面我没有具体的资料,但确实解放初期,我们扶风乃至宝鸡很多文化名人,政治名人都在贤山书院上过学。
我一度以为南官小学就是当年的贤山书院的后身,如果真是,那么我也算是贤山书院的学生,但前几天问过一个村里的老人,他却说不是,这让我一方面有些失望,另一方面有些疑惑,为什么不是呢?我小时好像听人说贤山书院在解放初还在运行,村里很多老人,包括我的父亲都是在贤山寺上学的,后来搬移到现南官小学的地方。我小时在里面上学,常常被墙上古怪的花纹吓的不敢去学校太早,总要等同学多了才进教室。
杨**,我的爷爷,故去很多年了,不提名。在我记忆里是一位留着胡须的慈祥老人,他在贤山寺的沟里,修了很多路,种植了很多树木,现在贤山寺沟壑里的树木丛生,林木丰茂,是有他老人家的功劳的。他种了一片梨树园,在我小的时候,是乐园,现在已砍伐。还有一片片的柿树林,现在还存在。还有嫁结的枣树,现在秋天去,还经常能采摘到青白的大枣,那味道一直留在我的舌尖上。甚至还种上了黄花菜、牡丹花,以前常开,现在是找不到踪迹了。
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八罗汉洞前有三株杏树,一株李树,一株老梅。杏树现在还在坍塌的洞前长着,梅花树却因移进寺内死亡,那株梅花最可惜了,有碗口粗的主枝,一到冬天,霜雪齐下,黄梅怒放。这曾一度是我的精神支柱,一直被我掂记。曾作文《古寺那株梅》记之,发表在《宝鸡日报》,在该文中我曾揣摩过梅的岁次,当然是散文的写法,不必过于较真。
前几天和村里一老人聊天,得知这几棵树居然也是我的爷爷所植,有点震撼。
杨宗望,我的伯父,当地有名的工匠,重修贤山寺时,寺中大雄宝殿就出自他手,院中重建贤山寺碑刻中有他的名字,现年过七旬,健在。
香山居士,南官村人,曾隐居香山,通岐黄术。后居贤山寺宝鸡峡渠道边,在八九十年代,人们普遍贫穷,病痛无钱可医时,他以几支银针,为百姓解病痛之危,不收分毫,一时周边几十里地人,都蚁行前来。他还广收弟子,只要立志能学,就可入门墙,给当地培养了不少医学方面的人才。并有数名弟子进入了省立市立大医院,成为专家教授。
我也曾受教门下,学习针石方法,深得老人喜爱,但后因家计困顿,父母阻挠,终止对中医的学习,深入南方,为馒头奋斗。老人去世时,我在南方,没人告诉我,知道时,已是五年之后,有悔有愧。
我和老人的感情很深,这是时隔多年后,我带着我的孩子去看老人坟茔的原因。
杨本善,南官村人,一直住在贤山寺的梨园小屋内,以守园为业。人之初,性本善,这是他的名字的来源。香山老人的大弟子,幼时伤残,单剩左臂,性执骜,人聪慧。他随老人习医,左手执笔,醮泥水,刷墙为字,居然珠圆玉润,让人佩服,幼时我常常站在他身后,看他写字,几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。没有多久,他就能以针除病,且屡有奇招,声名鹊起,逐以行医为生,常远游,后不知所终。距今二十余年了,杳然无音信。
这些人,都算是和我记忆里的贤山寺有关的人,历史上的人基本上是听来的,现实中的人都是我认识甚至亲密接触过的人,借这个机会,把他们一一记录下来。
古代的贤山寺,文字记录有限,所以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神秘。现在的贤山寺大约可以分两个阶段。我小时的贤山寺经历了重修的过程,这个在拙文《风雨贤山寺》有大约的记录。那时的贤山寺香火之盛,绝对超出一般人的想象,平日里人迹不断,如果逢农历大年,从初一到十五,还有农历七月十五过会,可以说是人挨人,人挤人,用文话说就是摩肩接踵,和现在初一法门寺的感觉是没有二致的。从南官村到贤山寺的路上,人也是一溜两行,那时我家的老屋子刚好在路边,也以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就是接待很多讨水喝或者要上厕所的行人。那时寺里的供养也很富足。
现在的贤山寺,寺门紧闭,别说外地人,就我一当地土著,对寺内的一树一木,一门一窗,比自己家里还熟悉的人,也不得入。今年我一人去贤山寺的那次,也只是绕寺一周,拍了几张大门的照片带回,没到寺内去。
为了这次的周五主持群里探讨贤山寺的事,我特意向村里一位老人请教了关于贤山寺的情况。得知,其实现在贤山寺所处的范围缩的很小,差不多是原来的十分之一。原来沿现在南官村西组的宝鸡峡以南的范围,都是贤山寺的范围。有一些塔,有一些殿堂,都在这些范围内,老人说他小时顽皮,还弄过殿内关羽的那把大刀。他说的这些,在我记事时是没有看到的,都拆毁了。
贤山寺的劫难我知道的有两次。一次是文革中拆掉所有建筑,木料砖瓦都运去盖了现在的南官小学和午井镇政府。这个我没有亲历。不过我小时上学的学校,确实有很多旧砖旧瓦,还有校门前的青石条,上面都有花纹文字,现在都不知所踪,很是可惜。另一次是村里的几个年青人在大约1992年底,打劫了贤山寺。事是真事,亦无亲历,是听说,但村里那一年一下子有六七个年青人被逮捕判刑,我都认识。据说他们用房上的瓦打狗,用院里的铁杈刺和尚,用砍柴的斧子劈开功德箱,大约是上了贤山寺的历史记录了。贤山寺的没落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呢?不得而知,因为也差不多是那一年,我离开了陕西南行,十几年后再回来,贤山寺的门就一直关着,也再看不到香客络绎的景象了。
贤山寺的将来。虽然我对佛教一知半解,但我觉得作为一座寺院,尤其是这样有名的一座寺院,他所肩负的不仅仅是寺内僧人自修的责任。佛教本身应该身负教化大众的职责,所以打开大门,还是比较合适的。

 污话社
污话社
 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
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 难得孤独
难得孤独 雪后登乌云界
雪后登乌云界 用笔记本记录美好生活
用笔记本记录美好生活 春天的一封信
春天的一封信 打造“超长待机“能力
打造“超长待机“能力 绝不天真,绝不退场
绝不天真,绝不退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