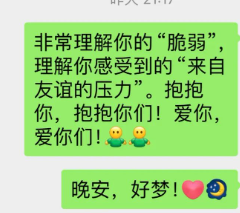农历十月初一,是过了七月十五中元节,又一个祭祖上坟的日子。这一天又称为“烧衣节”,在上坟祭祀时,人们把冥衣焚化给祖先,叫做“送寒衣”。世间活着的人,一年的耕收忙碌基本告停,冬天到来,开始准备御寒的衣物,当然也不会忘记在另一个世界的祖先灵魂也需要加衣添暖。
其实不过是一个习俗,那个世界到底存不存在是次要的,重要的是假若真有,希望亲人在那个世界里别再像这个世界那么艰难,那么孤独……
行走在小城的街上,一眼看到街口、路边摆满了黄、白各色的纸钱,眼眶里的泪一下子就止不住流了下来……
母亲去世半年,肺癌晚期,从发现、确诊,到亡故不足五个月。我这个不孝儿,没为母亲争什么气,也没给母亲多少欢。他乡路,一走几十年;床前孝,不足几日月。“慈母万滴血,生我一条命。”半生尽为我,未及报母恩。我应算个罪人。
妈不做官、无买卖,妈就是个最平凡的农妇,一生都累在地上,忙在家里;妈生在穷家,又嫁进一个穷家,受了一世苦,为了一辈子难,流了一生泪,生了半辈子气,操了半生心。
“苦日子过完了,妈却老了。好日子开始了,妈却走了。”
这就是我苦命的妈。从妈走的那一天我知道“这辈子我这儿已经做完了,从此后,我成了一个没妈的孩子。”
而至于人们说的下辈子,我不知道真有没有,更不知道做妈儿的福份,还不知道有没有资格轮到。
如若有,又怕再做了妈的儿子,还要让她受一辈子的累,操半辈子的心,这样的儿又何苦再去累她。
妈生我那年,村里的日子刚刚解决温饱,所谓温饱,不过是一天三顿的玉米饼子、玉米粥。临产前,半夜里,妈被一辆老牛车拉到十几里外的乡卫生院,一路大雪,妈忍着痛,挺到黎明六点钟,生下我。身子已虚弱得只剩下呼吸,母亲得到的营养与奖赏,就是一包红糖。
妈说,是那包红糖救了她的命。
月子里,妈没奶,急得直骂自己不争气。咬着牙,试了各种折腾人的“偏方”,都没奏效,妈流着泪从包裹里翻出她唯一值钱的嫁妆,一只成色不怎么好的玉镯子,叫父亲卖给当时村里的教书先生,给我换奶粉。那时候,没什么婴儿配方奶粉,乡下能买到的就只有一种,“草原牌”奶粉。
只是这玉镯子换来的奶粉,我也没吃到妈出月子,乡下都说“月子不出门”,可妈没办法,妈急!妈包好头巾,用小棉被里三层、外三层裹了我,深一脚、浅一脚踩着雪路,走遍村子里有小孩子的胡同,挨门挨户,为我求一口奶吃。而母亲对人家的回报,是回来后,一日一夜地为人家的孩子做大大小小的各种衣服、鞋帽。煤油灯下,妈穿了多少针线,已无法计数,如若计算,我想也能是一个“长征”。
我长至五、六个月大,食量变增,加之村里也没有几户有奶再求,母亲只好用小米粥喂我,妈说,头几日,我吃了吐,吐了吃,不肯下咽,急得“哇哇”哭红了脖子,妈也哭,但她没办法,一声声央求,到最后狠心,不吃就饿着,饿透了,没什么不吃的道理。
妈的狠,也是因为疼,咽着愧疚的苦,还得挺着艰难的累。生儿、养儿,妈愿什么都舍下。
好在,熬到一岁,我已能像大人一样进食,长得倒也白白胖胖。
妈要下地干活,哄我睡着之后,把我锁在家里,在炕沿围了好几层被子。但我醒了之后,还是爬着摔下炕头。妈下地,半截腰里不放心,路回来看见摔得满脸是血,扒着门槛已哭得没劲儿的我,放声大哭,从那天后,她剪下半截口袋做了个背袋,背着我下地干活。
这一背,就背到两岁。一场急来的雨,把我和妈浇了个湿透,我发烧烧到抽起风来,妈吓坏了,急疯了。一路背我到乡卫生院,半夜里,我醒了,跳下病床,光着小脚丫好奇地走到病房走廊里,拿起昏睡的值班大夫的听诊器玩,“啪”地一声掉在地上,惊醒了大夫,大夫把我抱回病房,妈趴在床边睡着,也许是有感应,妈惊呼一声“雪生!”,猛地站起来,一眼看到医生怀里抱着的我,抢几步过去抢过我,又笑了“雪生好了、雪生好了,谢谢大夫、谢谢大夫,我们雪生没事了是吧……”
这些我没“记事儿”前的事,是妈临走那几日忍着癌的巨痛折磨,精神恍恍惚惚之下一句、半句地念叨出来的。妈啊!是你还舍不得儿,是你做儿的妈还没做够……
妈这辈子很少跟我着急,印象中就急过两次。一次是我淘气,去邻居张奶奶家的房顶偷拿了人家的晒的枣吃,妈知道了,第一次发火,用鞋底子在胡同里抽了我的屁股,打完我,向人家连连道歉后,扯我回家,刚进家门,她也哭了。第二次,是我去邻村上完小(完全小学),下大雨,没回家,跑到同学家去住,不懂事的我,没让同村的人给妈捎话儿回去。妈冒着雨找到同学家来,跟我急了,一边哭、一边打,问我干嘛这么野。我还在人家同学家吃的腊肉饺子,饱饱的肚子一下子全剩下委屈。
妈着的这两回急,叫我以后有了两个记性:一不拿别人东西,二到哪里要给妈个知信。
这两件事,妈也记着,后来跟我说过,她说,我不打你,将来在外面你就会叫别人打;妈说,你去哪里,得叫妈心里有个底。
小时,我不懂这其中的深意,长大后,我分明地懂了:妈打我,疼在她手,若被别人打,疼在妈心;到哪里,要给妈个知信,是妈心里牵着一根线,她得知道线的那头有我,她心里才踏实。
妈这辈子,一直在苦日子里过,难日子里滚,没个停闲,也没个欢喜,苦和累都把她的笑压没了。
我考上专科那年,要拿几千块钱学费,家里凑不齐,好多人也劝“也不非上学这一条路”,但妈咬着牙把家里的耕牛卖了,说“这学,得上!”说得不容争辩、不容阻拦。
至今,我都难以想像,在那还没有农机的年代,妈是怎么把家里的十几亩地耕种过来的,跟人家谁家借了多少回耕牛,求了多少次人,又用什么还了人家的人情。
这事,妈没说。一直没说。
六岁那年,父亲在镇上的电机厂干临时工,一次跟一个老乡喝了酒后去上工,结果不小心被绞断了手。因为父亲违纪在先,厂里只象征性地给了点营养费,没给赔偿。从那以后,父亲终日唉声叹气,喝醉了就去厂里闹,闹也没结果,还被派出所关了两回。事情没闹出个结果,父亲就在家喝酒,渐渐养成了酗酒的毛病,喝多了,就撒酒疯,在村里得罪人,母亲跟着生没完的气,家无宁日。记忆中,母亲哭过不知多少次,也牵着我回过几次姥姥家,说这日子没法儿过了,但到最后,她也没离开过这个家半步。
专科毕业那年,好多同学分到了机关、政府,不行的也去了市里有名气的企业。我被分到了一个濒临倒闭的小破厂,工资都发不全。我陷入极度的悲苦,回到家也没笑容,妈看在眼里,也几日没说话。一日,我和同学喝酒,喝醉了回家,吐得满地都是,妈一边低头无声地为我收拾秽物,一边落泪……
到我第二天走,妈说:“怪妈没本事,只能靠你自个儿争气。酒别喝了,咱家已有一个酒疯子,再不能多一个酒疯子,你年轻,路还长,一辈子不能毁到一点小挫折、小委屈上……”
那次,我红了脸。

回到厂里,我狠下心,申请去新疆跑业务,因为可以多挣一点。我清醒地明白,我以后,成家立业,以后的以后,都得靠自己……
人生总有不期的困境,也会有柳暗花明的转机。我待的这个小厂非但没有如预料中的倒闭,反倒因为在新疆开拓了业务,受到政府的支持,厂子起死回生,还渐渐愈发壮大起来。因为我是第一拨儿去新疆的人,厂里对我挺看重,我便长驻新疆了。
有了积蓄,娶妻生子,安定生活,我没花家里一分钱。结婚那天,在村里摆酒席,妈穿上鲜亮的新衣,笑得满意、高兴。
然而人生充满着各种难以预料的不确定。后来,企业改制,我竟然成了第一批下岗工人,这对我犹如晴天霹雳的重创,不知为何,不知如何。
但事情来了,总要面对。下岗的事,我瞒了些日子,没跟妈说,直到我和几个哥们儿集资在新疆开了一个小厂子,才告诉母亲,说“国家鼓励下岗创业。”
但我们这个小厂子由于经营不善,没撑过两年,就资不抵债,集资的几个哥们儿也分行李散了伙。我又成了无业游民,我只好四处跑些散活儿,养家糊口,聊以度日。
这些事儿,我没跟妈说,我知道我也没法儿跟她说。我只让他知道,我在外面挣钱呢,到过年过节时能回来,这就足够了。
在外漂泊二十五年,挣下点辛苦钱,年龄大了,漂不动了,我生了回家的心,但回家总要给妈个安心的交待。
我把新疆的房卖了,回到家乡的小城,贷款买了套一百三十多平米的房子,另外用剩下的钱开了一家五金店,安顿生活。我是办妥这一切之后,才给母亲一个知信。我只说,咱有自个儿的买卖了,城里也有家了,以后接你到城里住,不种地了。
妈眼角一扬,没笑出来,但我分明知道那是她心里有了欣慰,儿子不再漂泊四方,有了安定的日子,回到了她的身边。
结果,房子装修好后,妈只是来看了一眼,就走了,说“你生意忙,我来了给你添乱,再说你这里我也住不惯,像个笼子,咱城里也没亲戚,我来了闷得慌,还是在村里住着自在些……”
一直到妈走,也没在我的新家里住过一夜。
后来,我不知妈从哪个老乡那里得知我的房子是贷款买的,从那以后,她就不停地在房后的一块空地上种菜,我每次回家,都让我满满地带回,有时候还托人给我捎来,说“小日子,就得精打细算,能省一分是一分……”
生意渐渐转好,贷款还清,车也买了。头一次开车回家,妈高兴地在村街上我的车旁边站了半天。人们都说:老太太你有福了,儿子在城里有房住、有买卖、有车开,以后你坐着你儿子的车,想去哪里去哪里……
妈只是笑,笑得有些努力、有些牵强,谦卑地说“就是做个小生意,也不发什么大财,踏实日子吧……”
我知道,是我该尽孝的时候了。只是我所做到的孝心,只不过是抽空回家看看,买一两样家用,母亲还直说我不该花那冤枉钱。我不知道,妈说的“冤枉”是要我节俭,要懂得算账过日子,还是她自己说的“我不用这什么、那什么名牌补品,吃五谷杂粮就行,我就是这个穷命,富贵东西我消受不了”。
但我分明地清醒,她的阻拦定是为我,而不是为她。
这就是我的妈。
而天下的母亲,无论权位、财富、贵贱尊卑,定也都是如此“妈妈给孩子的再多,也总觉得还有很多亏欠;儿子给妈妈的再少,也都说是孝心一片。”
可是妈啊,苦命的妈!你却怎么偏偏没有多让我尽些这些微不足道的“孝心”呢?
妈生我,万滴血;我养妈,日不足。妈啊妈,苦命的妈,你在临走前,神情已恍惚,还不放心地念着儿,念着儿早已忘记、或还没来得及知道的那些小事,我终于明白:我万般的小,在你那里都大于天,我就是你时刻不割不舍的心头肉……
哪怕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,无能为力,却还是不甘心!妈最后努力地叫着:“雪生啊……”我拼命地压抑着哭泣,却泪落如雨……
慈母十月万滴血,历险生我一条命。百千日夜养儿难,半生受苦尽为我。罪儿不及报母恩,痛心浊泪洒满街……
“有妈在,我们还都是妈的孩子;妈走了,我们成了没妈的孩子。”
世间贫富有别,也许我们的父母是贫穷的,或曾经贫穷,为我们准备的御寒衣帽不如他人之好,不如别人之贵。我们因攀比而烦恼,因为虚荣而抱怨。父母选择了原谅。甚至自责难过。直到有一天,我们也养育了儿女,才知道那其实已是父母给我们的最好,丝毫都没有偷减分毫。世间对“深爱”的定义,从来都不以多寡贵贱而论,而是“她有一,给了我们全部;她有二,给了我们所有。”
直到终有一天,她老了,叹息自己怎么这么快就老的不中用了,心里常常不安,怕给我们添麻烦,怕生病、住院、花钱,需要人照顾。她一辈子算账,一针一线,斤斤计较,到最后算到自己头上,想着能不累你,就不累你。
即便是累,但算算总账,到底还是她对我们的养育照顾更多、更长,少者二三十年,多则三四十年,还在帮我们。而她从病到走,不过十年、八年,或者更少。终归还是妈拖累我们的少,而我们欠她的多。
跪到坟前烧件衣,“妈,你在那个世界别冷着……”

 污话社
污话社
 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
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 难得孤独
难得孤独 雪后登乌云界
雪后登乌云界 用笔记本记录美好生活
用笔记本记录美好生活 春天的一封信
春天的一封信 打造“超长待机“能力
打造“超长待机“能力 绝不天真,绝不退场
绝不天真,绝不退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