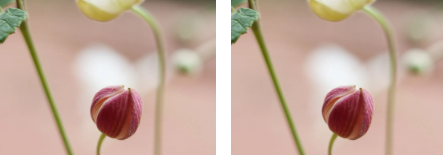第一次见到宋先生是她十二岁那年,宋先生推门进来的时候青色的长衫湿了大半,看来是行了远路。很少有人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显狼狈,偏偏宋先生就是。平时茶馆里只提供茶水和茶食,那日里恰还剩了一些面,通开火,煮了面端上来,汤清面白上面撒了翠绿的芫荽碗里还卧了一个荷包蛋。
宋先生微微诧异:“今天谁过生日吧?”
她抿嘴一笑,扭身上楼,留下一路轻快的足音。
早上雨停了,推开窗青石板路被清洗地熠熠生辉,河里的水也涨了不少。她磨蹭着梳了头下楼,宋先生已经走了。爹递给她一袋芝麻糖,说是那位先生送她的。
第二次见宋先生是她十三岁生日,说是行了远路在此喝杯茶歇歇脚。见她穿着簇新的衣衫头上插着簇新的簪子笑着说:“我妹妹跟你同岁,但她是个野丫头,可没你这么懂事乖巧。”说着拿出一个小小的铜铃铛,送给她。那个铜铃铛,做工精巧不说,温润光滑一看就是有年头的东西。看爹微微点头,她红了脸道谢。那天晚上,爹和宋先生聊到很晚。
生日总是让人期盼,宋先生的礼物也让她期盼,好在宋先生从未让她失望。每年她的生日,宋先生都恰好路过,每次给她带来一点小东西,有时候是一袋精巧的点心,有时候是个别致的小玩意儿:会翻跟头的猴子、带镜子的小盒子、笑容可掬的泥娃娃……
一年一年心里存了一丝念想,期盼着过生日期盼着见到宋先生,为了他来的那一天,她巴巴盼一年。那些礼物她都好好地收起来放在柜子深处,在无人的夜晚拿出来把玩。心里默默描画宋先生的样子,好像近在咫尺却总是看不清楚,仿佛隔了重重轻纱。每年他来了隔着门偷偷打量,又不是自己心里的模样。跟宋先生说些什么,没资格;扭身上楼,又舍不得。在年复一年的期盼里蹉跎了青春。众人都说茶馆老板的独生女儿怕是要找个上门女婿养老的,不然谁做媒都不成。爹说不用管他,只要合她的心意就好,可她始终不肯点头。
这一年的生日,宋先生又来了,照例要在茶馆吃过面住一宿再走。吃过饭宋先生低声问:“怎么不见老先生?”她低头不语眼泪一对对往下落不一会儿就打湿了衣襟。
宋先生叹息:“该找个婆家了。”
她低着头说:“我能养活自己。”
“遇到事有个人拿主意也是好的。”
宋先生起身推门,扭头看到窗边几案上的花:“这是什么花?怎么从不见开花?”
“昙花。一年只开一次。传说昙花是飞落人间的仙子,她在等她喜欢的人,把所有的美丽和芬芳集中在相遇的一刹那绽放。”
“哦,还有这种说法,那她等到了吗?”
“等到了。可是傻傻的等一年才开一次,宋先生,你说这样的等待有意义吗?”
“姑娘,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?”
“昙花。”
又一年,傍晚的时候宋先生推门进来,只看见一位年轻的掌柜。叫了一壶茶随意问道:“这里的昙花呢?”
“内子说那花不好养,再说一年才开一次。恰好一位路过的客人喜欢,央之再三,送他了,那位客人专程雇了船拉走的。”
“我是问那位开茶馆的姑娘。”
“那是内子,在楼上。”
夜深人静,夫妻二人相对而坐剥着罗汉豆。掌柜随口问:“今天有位客人来过,打问一位叫昙花的姑娘。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。”
“我一个女儿家,真名怎么能告诉他?还有的客人以为我的名字叫铃铛呢。”脖子上挂的铃铛没由来响了一下,“他留下什么话了吗?”
“没有。”
“留下什么东西了吗?”
“没有。”
门外的雨无声无息落着,门前的河水黑沉沉的,整个小镇淹没在这雨中,粉墙黛瓦如同一幅水墨画。
人与人总是要分别的,没有谁和谁能相守一辈子,年少时指着月亮星星说“我们要做一辈子的朋友永不分开的”早已云散高唐水涸湘江。离别时没必要争个长短辨个是非,说说到底谁亏欠了谁,原本风轻云淡的一段时光最后非要弄得一地鸡毛满城风雨。最后的分别就像宴会上最后的一道菜,可以吃一份甜品,也可以喝一杯清茶,千万不要吃到一粒麻椒,之前再好的滋味都会被掩盖。宋先生是个聪明人,应该知道终此一生永不相见是最好的选择。海阔天空,前途无量是宋先生的世界;守着小小的茶馆家长里短是卖茶女的人生。
(2017年1月29日于苏州)

 污话社
污话社
 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
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 难得孤独
难得孤独 雪后登乌云界
雪后登乌云界 用笔记本记录美好生活
用笔记本记录美好生活 春天的一封信
春天的一封信 打造“超长待机“能力
打造“超长待机“能力 绝不天真,绝不退场
绝不天真,绝不退场